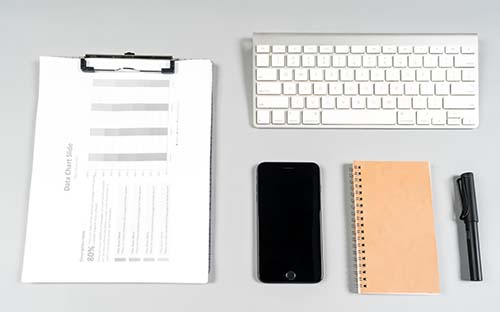嚴復留學時間_嚴復留學英國同學
接下來,我將針對嚴復留學時間的問題給出一些建議和解答,希望對大家有所幫助。現在,我們就來探討一下嚴復留學時間的話題。
文章目錄列表:
1.中日甲午戰爭后,嚴復提出的救亡思想的主要內容是什么?2.《嚴復》歷史評價與正史事跡,《嚴復》人物故事小傳
3.中國上世紀50年代以前留學英國的人文學者有哪些?
4.翻譯了《天演論》的嚴復,在擔任李鴻章的北洋水師學堂總教習時,痛斥軍中“迷信,搞裙帶關系”還有什么?
5.1877年,馬尾船政學堂畢業的嚴復等多少位去英國留學
6.較早通過翻譯西方著作向國人介紹西方社會進化論的學者是( )

中日甲午戰爭后,嚴復提出的救亡思想的主要內容是什么?
嚴復的“三民思想”是在維新運動興起之前就產生的。
早在1877—1879年留學英國期間,嚴復就廣泛研讀西方資產階級政治學術理論,并考察了英、法的社會實際,為其維新思想的產生奠定了基礎。1895年中日甲午戰爭中,清軍接連失利,在民族危亡的時勢刺激下,嚴復接連發表政論,提出變法救國理論。1895年3月上旬, 清軍在遼寧前線一敗涂地。嚴復于天津《直報》(一家由德國人漢納根所辦的中文報紙)發表《原強》;3月中旬, 日本逼迫清廷派遣李鴻章赴日談判,嚴復發表《辟韓》;5—6月間,清廷被迫簽約,舉國嘩然,嚴復又陸續發表《救亡決論》。在這幾篇文章中,嚴復首次提出了要將“鼓民力、開民智、新民德”作為自強之本。嚴復說:“生民之大要三:一曰血氣體力之強,二曰聰明智慮之強,三曰德行仁義之強。”西方政治學家“莫不以民力、民智、民德三者定民種之高下,未有三者備而民生不優,亦未有三者備而國威不奮者也。”(注:嚴復:《原強修訂稿》,載王軾主編:《嚴復集》第1冊,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18頁。)
由是嚴復考察了中國“民力、民智、民德”的狀況,得出一個基本的評價:“民智既不足以與之,而民力民德又弗足以舉其事。”(注:嚴復:《原強》,《嚴復集》第1冊,第15頁。 )進而大聲疾呼:“是以今日要政,統于三端:一曰鼓民力,二曰開民智,三曰新民德。夫為一弱于群強之間,政之所施,固常有標本緩急之可論,唯是使三者誠進,則具治標則標立;三者不進,則其標雖治,終亦無功。”(注:同④,第27頁。)“民智之何以開,民力之何以厚,民德之何以明,三者皆今日至切之務。”(注:同⑤,第15頁。)
嚴復將“鼓民力、開民智、新民德”提到極端重要的地位,并做了具體的闡發。首先,嚴復認為,衡量一個國家強富的標準在于“三民”:“國之強富貧弱治亂者,其民力、民智、民德三者之征驗也,必三者既上而后政法從之。”(注:同④,第25頁。)反之,如果“民力已恭、民智已卑、民德已薄”,(注:同④,第26頁。)則富強難行,甚至導向亡國亡種的境地。嚴復說:“使吾之民智無由以增,民力無由以奮”,被外族“奴使而虜用”、“彼常為君而我常為臣,彼常為雄而我常為雌,我耕而彼食其實,我勞而彼享其逸……”。(注:同⑤,第12頁。)那么,距“無以自存、無以遺種”的境地也就相差無幾了。其次,就中國的情勢而言,謀國救時的根本在于“三民”。嚴復指出,“民力、民智、民德”是“自強之本也”,(注:同④,第32頁。)圖強必須標本并治,“其本,則亦于民智、民力、民德三者加之意而已。果使民智日開,民力日奮,民德日和,則上雖不治其表,而表將自立。”(注:同⑤,第14頁。)“表者,在夫理財、經武、擇交、善鄰之間;本者,存夫立政、養才、風俗、人心之際。”“表必不能徒立也。使其本大壞,則表非所附,雖力治表,亦終無功。”(注:嚴復:《擬上皇帝書》,《嚴復集》第1冊,第65頁。)
那么,“三民思想”的具體內容是什么呢?嚴復提出了三方面的具體主張:
所謂鼓民力,主要是禁止鴉片、纏足,使人民體質增強,有強健的體魄,作為提高民智和民德的基礎;
所謂開民智,主要是廢除八股,提倡西學,使人民打開眼界,掃除蔽障,啟迪新知;
所謂新民德,主要是創立議院,各級官吏由公民選舉,以改變封建專制,使人民養成愛國公德,“合天下之私以為公”。(注:同④,第31頁。)
由此可見,與康有為、梁啟超等人的志趣不同,嚴復從一開始就將著眼點放在“民力、民智、民德”這些國民主體的革新上面,深刻認識到中國的救亡問題,其根本在于國民主體的程度的提高。從這一點出發,嚴復提出的“鼓民力、開民智、新民德”的救國主張,是一種貌似緩進、實則堅實的獨到之見。這一思想,同時也決定了嚴復在戊戌變法時期的具體表現,呈現出獨特的特點,當其他維新志士致力于政治活動和制度變革時,嚴復卻以發表政論、提供思想為己任,并且他的思想比康、梁等人的政治活動具有更為持久的影響力。
二
引起人們關注的,是戊戌變法失敗后嚴復思想所經歷的巨大變化,包括他對戊戌變法的反思和對辛亥革命的態度。從表面上看,嚴復在各方面都趨于保守,從批判封建專制轉向反對共和,從提倡資產階級新學回到封建主義舊學。但是,在這種表象的背后,被人們所忽視的,是其對“三民”思想的堅持和發展。
戊戌變法過程中。嚴復并未參加比較重要的政治活動,僅蒙光緒帝召見一次,略陳變法對策。事后應光緒帝之命,繕抄《擬上皇帝書》準備呈進,但尚未完成而政變已經發生。變法失敗后,嚴復感慨“臨河鳴犢嘆,莫譴寸心灰”,(注:嚴復:《戊戌八月感事》,《嚴復集》第2冊,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414頁。)幸而與康梁關系不甚密切,免于株連。但嚴復自此更為遠離政治旋渦,潛心于教書、譯書、著書,繼續為實現中國的富強做奠基的工作。1900年義和團之役后,嚴復避居上海,脫離水師學堂和海軍界,專心譯書。在清末的最后幾年,嚴復先后翻譯出版了亞當·斯密的《原富》、約翰·穆勒的《群已權界說》和《名學》、斯賓塞的《群學肄言》、甑克思的《社會通詮》、孟德斯鳩的《法意》等西方社會政治學術著作,并寫下了許多精辟按語。1906年,自著《政治講義》。在這些著作中,嚴復進一步表述了他的“三民”思想。嚴復繼續強調,要使國家得到真正的治理,仍要從“三民”入手:“所恃以救國者民,而民之智、德、力皆窳,即有一二,而少數之不足以勝多數,又昭昭也。”(注:嚴復:《〈法意〉按語》,《嚴復集》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958頁。)“夫民德不丞,雖有堯舜為之君, 其治亦茍且而已,何則?一治之余,猶可以亂也。”(注:同①⑥,第969頁。)嚴復還深入闡明了“三民”與民主的關系。嚴復承認,民主是“治制之極盛也”,(注:同①⑥, 第957頁。)但民主卻不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而是“民智最深民德最優時事”。(注:嚴復:《〈原富〉按語》,《嚴復集》第4冊,第891頁。)因為“斯民之智德力,常不逮此制也”。民主的第一要求是平等,而“平等必有所以為平者,非可強而平之也。必其力平,必其智平,必其德平”,如果做到了這三點,那末,“郅治之民主至矣”。(注:同①⑥,第957頁。)“未見民智既開、民德既蒸之國,其治猶可為專制者也。”(注:同①⑥,第986頁。)
為了提高中國民力、民智、民德的程度,嚴復將眼光投向了教育。1902年,在與《外交報主人論教育書》中,嚴復提出中國三大患在愚、貧、弱,三者之中,“尤以愈愚為最急”。(注:嚴復:《與〈外交報〉主人書》,《嚴復集》第3冊,第560頁。)1905年,嚴復因開平礦務局訟事赴倫敦,孫中山此時也恰好在英國,特意前來拜訪。這是兩種救國方案的一次頗具象征意義的會面,嚴復不能贊同以孫中山為代表的資產階級革命派正在為之不懈努力的革命救國方案,而堅持自己的“三民思想”,堅持教育救國。嚴復告以孫中山說:“以中國民品之劣,民智之卑,即有改革,害之除于甲者將見于乙,泯于丙者將發于丁。為今之計,惟急從教育上著手,庶幾逐漸更新乎!”(注:嚴璩:《侯官嚴先生年譜》,《嚴復集》第5冊,第1550頁。 )嚴復自己也投身于教育救國的事業之中,大量西方政治學術著作的翻譯和介紹,其根本目的,就是要使后輩青年洞識中西實情者日多一日。
然而歷史的發展正如嚴復所預料的兩難:“民智未開,則不免于外侮,民智既開,則舊制有不可行,行則內亂將作。此不易之道也。”(注:同①⑥,第979頁。)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推翻清室, 建立了民國。對于這一場驚天動地的社會變革嚴復是怎樣看待的呢?
耐人尋味的是,嚴復對辛亥革命和共和制度均不以為然。嚴復很早就“以革命為深憂”。(注:嚴復:《與熊純如書》,《嚴復集》第3冊,第610頁。)在嚴復看來,所謂革命風潮, 導致各種魔怪“悖然放肆,求以自快其意而不可御”,(注:嚴復:《〈古文辭類纂〉評語》,《嚴復集》第4冊,第1218頁。)只會破壞秩序,帶來災難。 嚴復是反對這種暴風驟雨式的革命的,認為“中國立基四千余年,含育四五百兆,是故天下重器,不可妄動,動則積尸成山,流血為渠。”(注:嚴復:《與熊純如書》,《嚴復集》第3冊,第632—633頁。 )武昌起義一爆發,嚴復就警覺到“吾國于今已陷危地”,在給張元濟的信中說:“東南諸公欲吾國一變而為民主治制,此誠鄙陋所期期以為不可者。”(注:嚴復:《與張元濟書》,《嚴復集》第3冊,第556頁。)他還致書英國記者莫理循,指出如果革命黨人“輕舉妄動并且做得過分的話,中國從此將進入一個糟糕的時期,并成為整個世界動亂的起因。”(注:絡惠敏編:《清末民初政情內幕——〈泰姆士報〉駐北京記者、袁世凱政治顧問喬·厄·莫理循書信集》上卷,知識出版社1986年版,第 784頁。)
嚴復認為共和國體不適合于中國。嚴復對世界政治進行了比較,結論是:共和政體在歐美諸邦也是不得已之制度,從效果來看,“亂弱其常,治強其偶”,(注:嚴復:《與熊純如書》,《嚴復集》第3 冊,第662頁。)就中國來說,地大民眾,尤其不適宜采共和政體。 他堅決不相信“以中國之地形民質,可以共和存立”。(注:嚴復:《與熊純如書》,《嚴復集》第3冊,第644頁。)武昌起義爆發后,嚴復曾“直接了當地說,按目前狀況,中國是不適宜于有一個象美利堅合眾國那樣完全不同的新形式的政府的”。(注:同②⑨。)甚至在共和告成已久,他還設想,“現在一線生機,存于復辟”。(注:同③⑩。)
正因為如此,嚴復在后期的著述里,對辛亥革命頗多微詞,反復強調辛亥革命是一場錯誤,對革命黨人也屢屢表示了切齒之痛,斥之為“乳臭夷奴”(注:嚴復:《與熊純如書》,《嚴復集》第3冊,第708頁。)、“四萬萬眾之罪人”,(注:嚴復:《與熊純如書》,《嚴復集》第3冊,第711頁。)是“以什百狂少年,掀騰鼓吹革命之變”。(注:同③⑤。)在他眼里,辛亥革命帶來的決非福祉,而是災難。革命使“世事江河日下”,“恐后之視今,有不及今此視昔也”。(注:同③⑤。)一言蔽之,“革命共和其大效今日可見,群然苦之”。(注:嚴復:《與熊純如書》,《嚴復集》第3冊,第713頁。)當然,令嚴復更傷感的是,他孜孜以求的強國根本——教育,在革命以后,“不特彈無,聽亦無矣”。(注:嚴復:《與熊純如書》,《嚴復集》第3冊,第624頁。)
三
這便形成了近代史上一個值得深入研究的現象。嚴復年輕時留學英國,廣泛接觸西方資產階級的政治思想,致力于西學救國,曾是中國思想界最先進的一分子。他的牛馬體用之喻對打破中體西用論起到了振聾發憒的作用,甚至被認定為全盤西化論者。他的思想曾經一度超前于中國現實社會發展的可能,有論者指出,當嚴復提倡民主立憲的民治主義時,“似乎除了少數人以外,得不到大多數人的擁護”(注:周振甫:《嚴復思想述評》,中華書局1936年版,第3頁。)然而時過境遷, 當歷史的潮流已經選擇了共和革命時,嚴復卻成了反對革命、反對共和制度的保守人物。但是,嚴復晚年政治觀念趨于保守,包括反對辛亥革命和共和制度,和封建頑固派是截然不同的。嚴復不是從祖宗之義、圣賢之訓來反對革命和共和,其政治態度變遷的思想根源,就是他的“三民”思想。
嚴復對戊戌變法做了深刻的反思。誠然,他對于變法的夭折深以為痛,但同時也認識到,沒有民力、民智、民德的進步,這種缺乏基礎的變法是難以奏效的。嚴復說:“民智未開,則守舊維新,兩無一可”,中國的前途,必須寄托在培養一批了解中西社會情形的智慧之士之上。如果洞識中西實情的人士日益增多,則中國“亦將有復蘇之一日也”,(注:嚴復:《與張元濟書》,《嚴復集》第3冊,第525頁。)“民智不開,不變亡,即變亦亡”。(注:嚴復:《與張元濟書》,《嚴復集》第3冊,第539頁。)
辛亥革命給中國社會帶來的變化自然遠遠超越了維新運動,但這一切并沒有影響到嚴復對其“三民思想”的堅持。辛亥革命發生后,嚴復把社會的進步仍然首先歸結為“國民程度”的進步。這個國民程度,就是他反復強調的“民力、民智、民德”。嚴復說,國家和社會的命運,“以民德為之因”,“其因未變,則得果又烏從殊乎?”(注:嚴復:《與熊純如書》,《嚴復集》第3冊,第611頁。)即使在形式上實現了共和,也只會是民主其表,專制其真,“民智卑卑,號為民主,而專職之政不得不陰行其中。”(注:同②③,第1551頁。)
那么,辛亥革命后中國的國民程度有沒有真正的提高呢?在嚴復看來,沒有。他痛感中國人的程度是“真不足”,(注:嚴復:《與張元濟書》,《嚴復集》第3冊,第556頁。)“真無足言也”。(注:嚴復:《與熊純如書》,《嚴復集》第3冊,第666頁。)或是“一旦竊柄自雄,則舍聲色貨利別無所營,平日愛國主義不知何往”(注:嚴復:《與熊純如書》,《嚴復集》第3冊,第620頁。)或是“看事最為膚淺,且處處不是感情之奴隸,即是金錢之傀儡。”(注:同④⑥。)這種程度的人民,是不適宜于民主共和的。嚴復以革命為深憂的道理即在于此,所以,武昌起義一爆發,他還親赴武昌,以國民程度不合于共和民主來勸說革命黨人。嚴復早就認為,使中國真正走向富強,只能漸變,不能驟變,在一切外緣內因皆不具備的條件下,“驟用新制,無異驅電車以行于蠶叢dié@①niè@②之區”。(注:嚴復:《說黨》,《嚴復集》第2冊,第299頁。)他在致莫理循的一封長信中明確表示,“中國人民的氣質和環境將需要至少三十年的變異和同化,才能使他們適合于建立共和國。”(注:同②⑨,第785頁。)所以嚴復所追求的, 是要創造一個安定的秩序,切實提高國民程度,繼續“鼓民力、開民智、新民德”,“但愿自今以往,稍得寧謐,俾以休養蘇醒,漸企高等程度之民,則如天之福也。”(注:同④③。)
不過,反對共和,與擁護封建專制應當明確地區分開來。確實,嚴復也說過“天下仍須定于專制”(注:嚴復:《與熊純如書》,《嚴復集》第3冊,第603頁。)的話,(注:嚴復:《與熊純如書》,《嚴復集》第3冊,第603頁。)但這僅僅是從專制有“恢復秩序”的功能而言,不是政治學意義上的“專制”。嚴復希望漸變,卻不是不變,而是在不引起社會動蕩的前提下,把封建專制漸漸引導向立憲政體。在武昌起義后大局未定的情況下,嚴復曾根據文明進化論的規律,提出“最好的情況是建立一個比目前高一等的政府,即:保留帝制,但受適當的憲法約束。應盡量使這種結構比過去更靈活,使之能適應環境,發展進步。”(注:同②⑨,第785頁。)1915年袁世凱稱帝,嚴復不以為然, 雖被列名“籌安會”中,卻沒有多少實際的贊助。1917年張勛復辟時,嚴復曾抱有一絲希望,指出復辟后“刻不容緩者,實立憲而已”,“首改憲法,次集國會”,除了皇位統于一尊之外,其余“則于共和國體等耳”。(注:嚴復:《與陳寶琛書》,《嚴復集》第3冊,第504頁。)。可見,對于共和的一些本質內容,他是贊成的,只是考慮到國民程度,于避免引起破壞性的社會動蕩,嚴復不贊成采取激烈的革命手段,也不贊成廢除帝制。從這些可以看出,嚴復反對辛亥革命,與封建頑固遺老是存在本質的不同的。
嚴復的“三民思想”,是其救國主張的一個基點。為挽救民族危亡,近代各個階級的代表、各個政治派別的人士都提出了各自的救國主張,與康梁、孫黃等政治活動家不同,嚴復的“三民思想”代表了近代救國主張的另一路徑。
晚年嚴復政治上趨于保守,以“三民思想”來反對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這是一種明顯的失策。這反映了他對于近代中國社會矛盾發展的判斷已經遠遠落在了時代潮流的后面。清末民初,中國社會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矛盾已經提出了革命的要求,使得以激進方式展開的革命救國方案具備了歷史必然性,這已不是任何力量所能回避、放棄、遏制或告別得了的了。在這種形勢下,嚴復株守“緩進”之見,以“民力、民智、民德”的不足作為反對革命、反對社會進步潮流的理由,因此,作為中國近代進步思想的啟蒙者,在晚年被自己所參與啟蒙的進步潮流所拋棄,就嚴復而言,是一場個人的悲劇;就整個時代而言,則是一個值得深入探索的歷史現象,盡管這一現象不僅僅表現在嚴復一人身上。
然而另一方面,嚴復的“三民思想”同樣也具有較高的歷史價值。它提出了各種革命救國方案所未能解決的一個問題:國民程度的提高,或者說正是嚴復主張的“民力、民智、民德”的提高。資產階級革命派通過長期斗爭,最終以激進的方式推翻了帝制、建立了民國。但“重武輕文”一直是革命派救國方案中的致命弱點,也嚴重影響了革命成果的鞏固。嚴復的“三民思想”,正是革命派所忽視的方面,反映了嚴復對于這一問題的認識,比革命派要更為深刻。遺憾的是,在近代中國歷史上,這兩種救國路徑始終沒有能夠得到有機的結合。出現在歷史前臺的縱然是革命潮流,接連取得了政治上的不斷進步,但卻缺乏國民程度提高的基礎性支撐。而“鼓民力、開民智、新民德”及其以后出現的教育救國、科學救國思潮,只能處于歷史潛流的地位,沒有充分發揮為中國現代化奠基的作用。
嚴復的“三民思想”所產生的影響仍然是十分巨大的。它對于21世紀中國現代思想文化的走向,具有開啟性的意義。有論者列舉現代中國思想與嚴復思想變動相合之處,有五四以后的全盤西化、國民黨的訓政思想、30年代本位文化建設、專制政治主張,等等,(注:同④⑩,第2-7頁。)雖未為至論,確也是有的放矢。目前中國的現代化建設又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在制度方面取得種種成就的同時,我們也必須高度重視現階段“民力、民智、民德”的提高,重視教育和科技,為21世紀的發展打下了一個堅實的基礎。這就是今天我們深入研究嚴復思想的現實意義。
《嚴復》歷史評價與正史事跡,《嚴復》人物故事小傳
《嚴復》歷史評價與正史事跡,《嚴復》人物故事小傳
嚴復(公元1854—1921年)字又陵,又字幾道,晚號愈野老人,侯官(今福建福州)人。福建船政學堂第一屆畢業,留學英國海軍學校。曾任北洋水師學堂總辦。甲午戰爭后,提倡新學,反對頑固守舊。曾大量翻譯西方作品。其中《天演論》在學術思想界頗有影響。又能詩文。有《嚴幾道詩文鈔》、《嚴譯名著叢刊》等。
〔正 史〕
嚴復,初名宗光,字又陵,一字幾道,侯官人。早慧,嗜為文。閩督沈葆楨初創船政,招試英俊,儲海軍將才,得復文,奇之,用冠其曹①,則年十四也。既卒業②,從軍艦練習,周歷南洋、黃海。日本窺臺灣,葆楨奉命籌防,挈之東渡诇敵③,勘測各海口。光緒二年,派赴英國海軍學校肄戰術及炮臺建筑諸學,每試輒最。侍郎郭嵩燾使英,賞其才,時引與論析中西學術同異。學成歸,北洋大臣李鴻章方大治海軍,以復總學堂④。二十四年,詔求人才,復被薦,召對稱旨。諭繕所擬⑤萬言書以進,未及用,而政局猝變。越二年,避拳亂⑥南歸。
是時人士漸傾向西人學說。復以為自由、平等、權利諸說,由之未嘗無利,脫靡⑦所折衷,則流蕩放佚,害且不可勝言,常于廣眾中陳之。
復久以海軍積勞敘副將,盡棄去,入貲為同知,累保道員⑧。宣統元年,海軍部立,特授協都統,尋賜文科進士,充學部名詞館總纂,以碩學通儒征為資政院議員。三年,授海軍一等參謀官。
復殫心著述,于學無所不窺,舉中外治術學理,靡不究極原委,抉其失得,證明而會通之。精歐西文字,所譯書以瑰辭達奧旨。
其《天演論自序》有曰:“仲尼之于六藝也,《易》、《春秋》最嚴。司馬遷曰:‘《易》本隱而之顯,《春秋》推見至隱。’此天下至精之言也。始吾以為‘本隱之顯’者,觀象系辭,以定吉兇而已。‘推見至隱’者,誅意褒貶而已。及觀西人名學,則見其格物致知之事,有內籀之術焉⑨,有外籀之術焉。內籀云者,察其曲而知其全者也,執其微以會其通者也;外籀云者,援公理以斷眾事者也,設定數以逆未然者也。是固吾《易》、《春秋》之學也。遷所謂‘本隱之顯’者外籀也,所謂‘推見至隱’者內籀也,二者即物窮理之要術也。夫西學之最為切實,而執其例可以御蕃變者,名、數、質、力四者之學而已。而吾《易》則名、數以為經,質、力以為律,而合而名之曰《易》。大宇之內,質、力相推,非質無以見力,非力無以呈質。凡力皆‘乾’也,凡質皆‘坤’也。奈端⑩動之例三,其一曰:‘靜者不自動,動者不自止,動路必直,速率必均。’而《易》則曰:‘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有斯賓塞爾者,以天演自然言化,其為天演界說曰:‘翕以合質,辟以出力,始簡易而終雜糅。’而《易》則曰:‘坤,其靜也翕,其動也辟。’至于全力不增減之說,則有自強不息為之先;凡動必復之說,則有消息之義居其始。而‘易不可見,乾坤或幾乎息’之旨,尤與熱力平均、天地乃毀之言相發明也。大抵古書難讀,中國為尤。二千年來,士徇利祿,守闕殘,無獨辟之慮,是以生今日者,乃轉于西學得識古之用焉。”凡復所譯著,獨得精微皆類此。
世謂紓以中文溝通西文,復以西文溝通中文,并稱“林嚴”。辛酉秋,卒,年六十有九。著有《文集》及譯《天演論》、《原富》、《群學肄言》、《穆勒名學》、《法意》、《群己權界論》、《社會通詮》等。
《清史稿·嚴復傳》卷四八六
〔注 釋〕
①用冠其曹:因此把他列為第一名。曹,群,眾。②卒業:結業。③诇敵:偵察敵情。④總學堂:為學堂總辦。⑤諭繕所擬:命令他繕寫好草擬的萬言書奏上。⑥拳亂:指義和拳運動。⑦脫:倘或;靡:無。⑧道員:清代省以下,府、州以上的行政長官。⑨內籀之術:指歸納推理的思維方法。下文所謂“外籀之術”,則指演繹推理。⑩奈端:牛頓的音譯;動:指運動定律。
〔相關史料〕
嚴又陵哲學大家,人多知之,至其詩才之淵懿,或罕知者。余記其《戊戌八月感事》一首云:“求治翻①為罪,明時誤愛才。伏尸名士賤,稱疾詔書哀。燕市天如晦,天南雨又來。臨河鳴犢嘆,莫遣寸心灰。”又《綠珠詞》一首云:“情重身難主,凄涼石季倫。明珠三百琲②,空換墜樓人。”蓋哭林晚翠也。
梁啟超《飲冰室詩話》
〔注 釋〕
①翻:反而。②琲(bei):串珠。
中國上世紀50年代以前留學英國的人文學者有哪些?
朱自清,1931年到英國倫敦留學,修習英國文學跟語言學
周恩來,1921年到英國,成功申請愛丁堡大學,但未入讀
嚴復,1877年留學英國學習海軍,但其本人是思想學家跟翻譯學家
徐志摩,1920年到英國LSE,1922年進如劍橋
錢鐘書,1935年到英國牛津大學埃克塞特學院
周埈年,1910年進入牛津大學女王學院學習法律,并獲得英國執業大律師資格,曾任香港立法局及行政局的首席非官守議員
陳舜禮,1949年于牛津大學畢業,曾任天津南開大學教授,南開大學副教務長,山西大學教授,山西大學教務長,山西大學圖書館館長。1982年4月-1983年9月,擔任山西大學校長。政官至全國政協常委。
羅德丞,牛津大學畢業,曾任香港律師會會長,行政立法兩局議員,全國政協常委
王繩祖,1936年入讀牛津大學布拉斯諾斯學院,為歷史學家,國際關系史學家
許國璋,1947年留學英國牛津大學留學,名英語教育家、語言學家
翻譯了《天演論》的嚴復,在擔任李鴻章的北洋水師學堂總教習時,痛斥軍中“迷信,搞裙帶關系”還有什么?
中國近代化進程中不可不說的人物勢必有嚴復之名,嚴復(1854-1921)并未和大多數讀書人一起走科舉“正途”,而是由于家道中落于1867年進入福州船政學堂學習馭船之術。此時正值洋務運動開啟之時,清政府大力興辦新式教育、籌備海防,嚴復也因此不僅接受了傳統的中式教育,也接觸到了西學思維。1871以最優等成績畢業,服役于清軍水師。并因表現優異于1872年作為中國第一批海軍留學生赴往英國格林威治皇家海軍學院學習,七年后(1879)嚴復學成歸來開始投身教育,長期擔任天津北洋水師學堂總教習。由此來看,關于海軍方面才是嚴復的“本業”。
(嚴復)
嚴復最引人注目的地方即他所傳播的西學思想及譯著《天演論》,也因此容易讓人忽略他對中國發展過程中教育近代化和海軍發展所做的重要貢獻。其一貢獻在于嚴復在海軍教育方面的建樹。1880年初,嚴復在北洋水師學堂擔任總教習,完善了北洋水師學堂基礎教學方法,為北洋水師艦隊培養了大批優秀人才。同年八月,他受李鴻章邀請參與籌備天津水師學堂,并繼續投身海軍教育整整二十年。
(第一批福州船政學堂留歐學生)
其二貢獻在于嚴復的海權思想,他受美國馬漢海權理論影響并形成自己獨特見解。他認為海權對國家而言非常重要,直接關乎國家主權、國力貧弱和國際地位。建立海權不僅有利于國防力量的加強保衛國家主權,還有利于國民航海獲取利潤,能達到富國強兵雙重目的。并提出加強海軍教育培養人才,建設軍港、海岸炮臺等方法締造海權。
(天津水師學堂)
從最初投身于海軍教育對海軍建設人才的培養以及后期海權思想傳播,到甲午海戰北洋海軍全軍覆滅后嚴復對海軍建設提出的一系列建設要求,可以看出嚴復是對中國整個海軍建設進行過整體規劃的人之一,雖然這些想法并未被付諸,但不可否認的是他對海軍建設所做的努力加速了中國海軍國防近代化進程,因此也被被譽為“近代中國海軍人物中之典范”,可謂是當之無愧。
1877年,馬尾船政學堂畢業的嚴復等多少位去英國留學
我們金吉列留學無法確定1877年馬尾船政學堂畢業的嚴復等人去英國留學的具體人數。
然而,根據我所了解的歷史知識,馬尾船政學堂是中國近代一所著名的軍事學堂,旨在培養海軍和航運人才。該學堂的畢業生中有很多人曾前往英國留學,其中包括嚴復等著名人物。這些留學生通過在英國的學習和實踐,不僅掌握了先進的科技和軍事技能,也了解了西方文化和社會制度。
如果您對嚴復等人去英國留學的具體人數感興趣,建議您查閱相關的歷史資料或咨詢專業的歷史學家。金吉列留學作為您身邊的留學專家,始終關注著中國近代留學史和國際教育發展情況,為您提供更準確和全面的信息。點擊了解各國留學信息
較早通過翻譯西方著作向國人介紹西方社會進化論的學者是( )
較早通過翻譯西方著作向國人介紹西方社會進化論的學者是嚴復.
《天演論》的譯者是嚴復。清朝末年,甲午海戰的慘敗,再次將中華民族推到了危亡的關頭。此時,嚴復翻譯了英國生物學家赫胥黎的《進化與倫理》,宣傳了“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觀點,并于1897年12月在天津出版的《國聞匯編》刊出,該書問世產生了嚴復始料未及的巨大社會反響。
嚴復,初名傳初,字又陵,后名復,字幾道,福建侯官(今屬福州市)人。光緒三年(1877),嚴復作為清政府首批派遣留學英法的學員,赴英國學習駕駛。在英國格林威治海軍學院(后改名皇家海軍學院)學習的兩年半中,“考課屢列優等”,成為該校的高材生。
嚴復譯述《天演論》不是純粹直譯,而是有評論,有發揮。他將《天演論》導論分為18篇、正文分為17篇,分別冠以篇名,并對其中28篇加了按語。他在闡述進化論的同時,聯系中國的實際,向人們提出不振作自強就會亡國滅種的警告。
維新派領袖康有為見此譯稿后,發出“眼中未見有此等人”的贊嘆,稱嚴復“譯《天演論》為中國西學第一者也”。
好了,今天我們就此結束對“嚴復留學時間”的講解。希望您已經對這個主題有了更深入的認識和理解。如果您有任何問題或需要進一步的信息,請隨時告訴我,我將竭誠為您服務。

請添加微信號咨詢:19071507959
最新更新
推薦閱讀
猜你喜歡
關注我們


 留學規劃
留學規劃  留學考試
留學考試  留學指南
留學指南  留學攻略
留學攻略  留學生活
留學生活  留學信息
留學信息  留學專業
留學專業  留學簽證
留學簽證  關于我們
關于我們  網站首頁
網站首頁